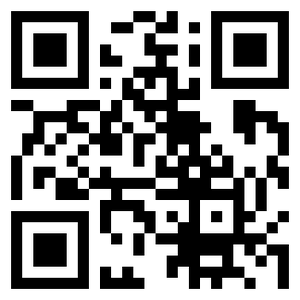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明利配资端
字数:4415,阅读时间:约12分钟
编者按: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年。金国铁骑南下,席卷中原,最终攻陷汴京,俘获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而在这场剧变中,榆次之战并非规模最大的会战,但却称得上是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它是北宋第一次东京保卫战后,为解太原之围而发起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大规模救援行动的终曲。
此战的惨败,意味着北方军事重镇太原的最终陷落,也让金军第二次南下彻底失去了军事上的掣肘。然而,这场在一定程度上关于北宋危亡的关键战役,如今流传下来的战役细节却极其混乱,不仅参战人数多寡众说纷纭,关于宋军主将种师中的败亡原因更是莫衷一是。在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认为种师中行军仓促,没有带够赏赐用的银碗,作战时麾下没得到赏赐的神臂弓手“相与散去”导致战败。

不给赏赐就不射箭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源于抗金名臣李纲的《靖康传信录》:“金人乘间讻突诸军,(宋军)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赏射者,而随行银碗只数十枚,库吏告不足而罢,于是士皆愤怨,相与散去。师中为流矢所中死之,其余将士退保平定军”。
诚然,这一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种师中这位西北名将的战死披上了一种悲剧色彩,但过于故事化的表达却无益于我们去了解这场北宋覆亡前夜的救援之战。

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此战救援的对象:太原府。
太原府,古称晋阳,地处山西高原中心,控扼太行、吕梁两山之间的河谷通道,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战略屏障。对于金军而言,太原犹如钉在其西路军南下侧翼的一颗钉子。不拔除太原,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南下汴京时,始终需要担心侧翼会受到太原宋军的威胁,后勤线也难以保障。因此,攻陷太原,是金帝国实现其鲸吞中原战略的绝对前提。
公元1125年末,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围攻太原;东路军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直扑汴京。北宋朝廷在惊惶失措之下,答应了金人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屈辱条件,换取了金军东路的暂时北撤。
然而,这一决定旋即遭到了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和三镇军民的强烈抵制。太原军民拒不开城,继续浴血奋战。此举在道义上值得歌颂,但在战略上却使北宋朝廷陷入了两难:既已“割让”,出兵救援便缺乏法理上的绝对正当性,且给了主和派口实;但若不救,则等同于自毁长城。
金东路军北撤后,西路军完颜宗翰却并未解除对太原的包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但在守将王禀的领导下,依旧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抵抗。这座历史上曾经让朱温、李从珂、柴荣、赵匡胤等枭雄吃尽苦头的龙城,再次将金西路军牢牢拖在城下。对于北宋朝廷而言,拯救太原的窗口期就这样出现了。

然而此时的宋廷却陷入战和不定的纠结当中,李纲等主战派纷纷上书,力主救援太原,巩固北方防线,否则金军卷土重来时明利配资端,将无险可守。而耿南仲等主和派却并不愿意放弃刚刚求来的“和平”,认为既然已经议和,再兴兵戈会激怒金人,且在恐金症的影响下,“朝廷缙绅上恬下嬉,幸于无事,恃以为安”,这些主和派对于这种救援显然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钦宗本人同样倾向于苟安,尤其是在姚平仲劫寨之战失败狼狈而逃后,钦宗本人犹豫不定,虽然在李纲的一再坚持下,钦宗最终还是做出了救援太原的决定,“诏河北三帅固守三镇,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但由于其本人的摇摆不定,这场姗姗来迟的救援整个过程都充满着犹豫、反复和掣肘。而这无疑为后续军事行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此后,“种师道为河北宣抚,驻滑州;而命姚古为河东制置,种师中副之;古总兵以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诸郡”,此时恰逢河东平阳府义胜军等部叛乱,引金兵入南北关,连陷威胜军、隆德府,兵锋直指泽州高平。
“恐金症”发作后,宋钦宗将诸将悉数召回,彼时姚古、种师中部距离金军只剩二十余里,却不得不奉诏班师。更戏剧性的是,诸将开始班师后,在得知消息的李纲与宋钦宗力争之下,钦宗再次改弦易辙,复遣诸将追袭,如此朝令夕改,宛如儿戏。前方诸将自此“悉解体矣,不再有邀击之意”。

靖康元年三月,河东制置使姚古率军收复隆德府、威胜军后,继续北上,与金军对峙于南北关,一时间无法突破。“大兵尚在威胜军,无一人一骑入太原境者”。为解围太原,宋廷计划姚古部自威胜军向北,种师中部则自土门路向西,两路大军共同支援太原城。这是北宋靖康时期第一次也是最有希望的一次救援计划。
不过,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这场最具希望的救援之战,其起因之仓促也颇为荒谬,同知枢密院事许翰得知“宗翰还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的情报后误认为金军“势穷力竭”,催促种师中、姚古出兵解围太原。
为迫使种师中出兵,许翰“从中督战无虚日,使者项背相望,诏书以逗挠切责师中。”所谓“逗挠”即怯阵避敌之意,将这样的罪名按在一个西军老将的身上,其行为已经颇具侮辱意味。
在许翰“昧于兵机,以峻文绳公,不容顷刻”的催促之下,不堪其辱的种师中不得不仓促集结部队,“辎重犒赏之物 悉留真定,不以从行”。种师中率军自从真定府出发,进入土门路,经天威军(今河北井陉)、承天军(今山西娘子关)、平定军(今山西阳泉),出土门路,向太原城逼近。

西路军占领河东要冲南北关后,已据此阻遏住宋军姚古一部,而麟延路军马使黄迪与陕西将领王迪等会兵进至河东汾州上贤,为金人所败。到了五月盛夏,不耐酷热的金军主力在宗翰的调动下回云中避暑,只留有完颜银术可等部继续围困太原,而在汾州、滁州等地,也留有部分军队阻击北宋援军部队。
但宗翰毕竟对于河东地形熟悉程度不足,在布防之时,未能注意他眼中“不能通车马”的井陉路,而这也是种师中部出援太原的通道。
这一出乎预料的援兵让正在太原围城的银术可部惊慌不已,《三朝北盟会编》称“不谓师中由平定出关,一旦去太原,不远一舍,贼众惊惶,谓自天而下。”回顾北宋对太原的数次救援之战,种师中部自井陉西,无疑是北宋最接近战略目的的一次时机。
为了防止种师中部与太原守军合流,金军在获得种师中部援军消息后,多次派兵阻遏其行军,在前进至榆次县途中,双方自寿阳石坑处开始总计接战五次,种师中部五战三胜明利配资端,已然是稍占上风。相比于金军南下以来的摧枯拉朽,种师中部此时可谓是高歌猛进。
但此时,榆次之战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记载出现了,《宋史·种师中传》载:“五月,(种师中部)抵寿阳之石坑,为金人所袭。五战三胜,回趋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 灏失期不至,兵饥甚。敌知之,悉众攻”。
按照《封氏编年》的记载,种师中部到达寿阳石坑并与金人接战后,“前军已到石桥,至太原止二十里”,有人认为,如果种师中在此时挺近太原,未必没有机会在守军的接应下进入太远城内的机会,若援军抵达,即使抛开实际物资、军力层面上的补充,仅仅是支援到来的士气影响,就足以再次为太原守军续上一口气。

令人叹息的是,种师中却在此时选择了回返榆次,等待姚古等部汇合。后世在复盘榆次之战时认为,种师中的回返并非毫无原由。
前文提到,宗翰领大军返回云中避暑,这一行为让当时宋军斥候误以为金军已然力尽,这也是为何朝中文臣屡屡催促种师中立即出援的原因之一。这一错误信息未必误导了种师中,但种师中部在抵达寿阳前“节次斩获金人首级,开通道路”的顺利无疑让这个老将产生了些许误判,让他错误估计了敌人对他这一支援军的阻力强度。
但在寿阳石坑前后接连五次与金军发生交战,则让这位老将军意识到金人已经在集结军队,更可怕的是,由于这几支金人部队的阻碍,本就轻装上阵的宋军部队才真正到了势穷力竭的地步,据《靖康小雅》的记载,种师中之所以回军榆次,正是因为补给不足。“金人先屯兵(榆次)县中,公遣击走之,遂入县休士,时军中乏食三日矣。战士日给豆一勺,皆有饥色。”
这里面,“公遣击走之,遂入县休士”的记载正好能与《宋史·黄友传》相印证,前军参谋黄友奉种师中之命,带兵攻榆次得粮万余斛。可以想象,如果这支已经乏食三天、日给豆一勺的疲兵,能够在榆次当地得到一定的休整,未必不能成功驰援太原。
但历史并没有给予种师中多余的时间,就在攻下榆次的翼日,尚未恢复的宋军就遭遇“金人以数万骑压之”的猛烈攻势。
李纲《靖康传信录》中关于神臂弓手和银碗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宋史·种师中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赏赉不及,皆愤怨散去, 所留者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

这样看来,两者似乎可相互印证。但根据《宋金榆次之战三题》的分析,《宋史》基本照抄了《三朝北盟会编》中“师中率麾下死战, 自卯至巳,所余才百余人。身被数枪,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的记录,并在中间加上了《靖康传信录》关于神臂弓手因赏赉不及愤怨散去的细节。
但如此一来,却彻底改变了《三朝北盟会编》关于宋军溃败的记叙愿意,《三朝北盟会编》原文如下:
金人娄宿(完颜娄室)悉兵来攻右军,右军先溃,前军亦奔。师中率麾下死战, 自卯至巳,所余才百余人。身被数枪,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
从这里来看,种师中“所余才百余人”,并非是因为神臂弓手赏赐不及,而是右军、前军在完颜娄室的攻势下悉数溃散,而种师中部独木难支,在支撑数个时辰后死伤惨重,仅余百余人。赏赐不及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宋军士气低落,但并非整支军队尽数溃散的原因。

榆次之战中,种师中唯一的失误,在于大军屯驻榆次时对金军战略意图的误判。种师中率军返回榆次时,驻大军于榆次城西十里之处。榆次地处汾河谷地的北部,除北面数十里外为山地外,其他三面均地势平坦,难以有效阻遏骑兵。
前军参谋黄友曾建议让大军入城,种师中并未采纳。如果据榆次县城防守,或许能避免遭遇金军骑兵驰突的危机。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老将,种师中不应犯下如此低级的失误。唯一的解释就是,种师中认为金军会龟缩至太原城下集结不再出击,所以希望迅速补充粮秣,与姚古部汇合后继续驰援太原。
这种对于局势的误判还影响到之后对于金军兵力的判断。完颜娄室在进攻种师中部时,“悉兵来攻右军”。可见种部应是右军在北,即靠近山地的那一面,意图自此切断宋军转进的通道,但种师中却以为榆次之敌为“(金军)残零将归者,令后军去捉收”。
这种对于军情的误判,代价极其残酷。种师中此时派去“捉收”的是刚刚与种师中部汇合不久,编制完整、士气尚足的张师正所领胜捷军,却在敌情不明之下和右军一道被金人击败。

至于如朱熹等人认为的,“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愤然赴敌以死”,只能说,这些文臣们似乎太过于小看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现实以及枢密院官员对于武臣的压制力了。
参考文献:
1、张兢兢《宋金榆次之战三题——关于双方兵力、战役时间、宋军失利原因的考证》
2、赵宇豪《宋金榆次之战考论》
3、李华瑞《宋金太原之战》
4、陈乐保《靖康年间宋军援救太原之战述论》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维度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